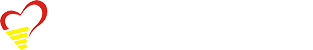| 深圳最后的 “支农者” |
| 刘启达 |
| ||
| ||
■ 深圳特区报记者 刘启达 文 图
“菜篮子”一直最受市民关注,近日台风导致了深圳菜价的波动,不少菜价直线上升,这也引起了家住南山丽湖社区的邱新贵的关注。
“以前每次台风来临,我们在深圳也是可以收获蔬菜的。”说这话的邱新贵有一个特殊身份,他是深圳最早的一批“支援农业建设者”,也是深圳最后的一批“支农者”。
邱新贵与深圳的故事发生在1982年。他带着一家6口来到南山西丽“支农”,31年过去了,他成了深圳“支农者”中的最后一批坚守者:在城市的边缘种田种菜,做着都市的生意,过着农民的日子,几十年不变……
结伴到深圳“支农”
1979年的广东农村经历重大变革,这年6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铺开,其中河源紫金县出现的单干户超过1.5万户。
时年29岁的邱新贵当时在紫金九树村当农民,他干劲十足,种田打耙、挖地开荒什么都干,但随着儿女的出生,老家人多地少的矛盾就出现了,一家6口只有2.4亩地,歉收时连口粮都供不上。
深圳经济特区建立那年,南下打工的人很多,蔬菜供应压力很大,邱新贵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,心中一怔:反正到哪里都是种地,那还不如到城市边上去种,这样赶个集都方便。
1982年上半年,深圳市提出组织外地农民到深圳“支农”种菜,先后到潮汕地区和广州郊区分别组织5000多菜农到深圳种菜,邱新贵正好赶上了。
邱新贵先和几个老乡在深圳西丽的大磡探点种地,稻谷、花生、红薯……什么都种,有了收成就拉到南山市场去卖。邱新贵记得当时花生每斤能卖到1.5元,这一年光花生就卖了500多斤。
年后,邱新贵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,他决定和妻子刘祝英带着4个孩子赶赴深圳“支农”,做一个“永久居民”。与邱新贵一道的还有邱增云、邱育森、邱金台等7户人家共40多口人。
关上老家土砖房的柴门,他还特意在门上挂了把新锁,邱新贵希望自己能回来,但他自己心里也着实没底:当了几十年农民,现在背井离乡,怕是再也不回来了。
关门、上锁,离开九树的那一刻,邱新贵洒下几行热泪……
种菜业绩上过《人民日报》
邱新贵一行人最后浩浩荡荡开进南山大磡村。
邱新贵回忆说,眼前的大磡村绝大部分是荒山,从南头到大磡村没有公交车,只能走路,而进入种植所在地王京坑,只能自己开出一条土路。
刚到大磡大家根本没有房子住,很多人只能睡在树下或者搭草棚住。邱新贵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建房子,砖、瓦都是自己动手烧。半年后,房子就建成了。一家6口才算在深圳有了栖身之地。
1984年经紫金县劳动服务公司和深圳南山区农牧公司签订协议,并经深圳市批准,邱新贵一行成立“支农”机构——紫金种养场。
邱新贵眯着眼回忆说:“紫金种养场红火的时候有近300农民同时干活,稻谷、蔬菜、花生、红薯……什么都种,市场上缺什么就种什么。在紫金种养场周围的‘支农’农场还有信宜种养场和淞口种菜场。”
后来,种养场还建起了党支部,蔬菜最高年产5万公斤,为特区农产品供应作出了贡献,并因此还上过当年的《人民日报》。上报的事过去几十年了,但邱新贵回忆起来还是津津有味,谈得眉飞色舞。
跟不上都市节奏
在农场里干活,邱新贵与妻子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依然保持了在老家的生活习惯,繁华都市近在眼前,但他们很少去逛街,只安心种田。
从远处传来的卡拉OK声隐隐能听到,但这与邱新贵家里无缘,孩子们只能在床上听一听,然后睡觉。
第二天清早,邱新贵就开始收菜,然后运到市场卖,几个小时后就能卖完回到种养场。
过了农忙,邱新贵就四处找些零工来做,帮人种荔枝、挖鱼塘、收稻子……帮人收一天荔枝挣15块钱,冬天帮人挖一天鱼塘挣50块钱,反正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。
妻子刘祝英也和在老家一样,在种养场以及门前屋后养了猪、狗、鸡、鸭,其他的农户甚至还养起了牛羊,每天清晨把它们放进荔枝林,夕阳西下的时候,一声呼哨,它们又成群结队地回到圈中。
邱新贵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龄,就送到附近上学,只是每年要多交1000块的借读费。女儿需要坐校车,本地的孩子是不用交车费,但她每月需要多交150块钱的车费,因为女儿是外地户口,她不能享受这些。
农闲时,刘祝英到附近的工厂帮人扫地挣点家用,与丈夫种田作息一样早出晚归。
邱新贵说,这里的生活与紫金老家没什么两样,只是换了一个靠近都市的新环境,“有力气就有钱挣”。都市繁华生活与快节奏在这里都不奏效,邱新贵更愿意与孩子们一道按着老家的生活往前走,一步一步、不变不惊。
记者昨日来到他们所说的这片荔枝林,一条土路直通荔林深处,随处可见的是水源保护区的告示牌。见有生人来,一群狗在荔林里狂吠,一位姓曾的阿婆安详地坐在路边放羊。再往里走,藏在荔枝树下的几户人家才显露出来。邱新贵说那里曾是他的家。
“支农”的坚守者
1995年,邱新贵还与另外6户人家一道承包了西丽湖边的近400亩荒山,承包的费用是每年上缴数万斤荔枝,邱新贵在那里挥汗如雨干了5年多,全部荒山都种上荔枝树。已当上副场长的邱新贵带着农民,固执地坚持着春种秋收的梦想。
随着深圳交通设施完善,货畅其流,外地农产品大量涌入深圳,城市扩张让“支农者”不断从城市撤退。2000年左右,“支农者”开始纷纷撤离,信宜场、淞口场先后消失。由于紫金场离市区较远,加上交通不便,紫金场一直保存了下来。
2001年前后,西丽水库被政府划为一级水源保护区,紫金场正好在这个保护区内,按要求,水源保护区里不能再搞种植与放养牲畜,邱新贵全家面临搬迁。
刘祝英哭着不想搬,因为再建一个家太难了,这里住了快20年了,感情上也不舍。因为这些房子都是没有报批的违建,况且这里是水源保护区,2009年初,城管将这里的建筑拆除。
这个时候,邱新贵和一些当年的伙伴回了一次老家紫金,想看看20多年前留下的老屋,泥砖老屋已残破不堪,当年的新锁已锈成烂铁。
邱新贵一家最后选择还在深圳打拼,又在水源区外建了一间房子,准备再在当年的400亩荒山上再努力耕种,多收荔枝,多养走地鸡。
这一年,邱新贵遇到了一个他无法绕开的土地权属问题。当年大家一起承包的400亩荒山承包期到2010年结束,但2001年前后此地被纳入一级水源保护区,一切种殖都受到限制,走地鸡只能养几只、牛不能再养了、农药不能再用了,一旦超过这个范畴,就会有政府的工作人员找上门来问责。
当年的7家人家,邱增云已投奔远在河源的儿子,邱育森跑到惠州与儿子一起搞修理,邱金台早已洗脚上田,在西丽开环卫车,邱卫荣回到紫金老家养猪,只有邱新贵还坚守在荔枝林里,他笑着说:“我是深圳最后一批‘支农者’”。
比没走出来的人强
有一段时间,紫金种养场因子弟成绩优秀也出了名。孩子们生活清苦,走不进都市圈,都知道埋头苦读,场里先后走出30多名大学生。但邱新贵家的孩子显然是一个例外。
邱新贵家里4个孩子除了小儿子读了中专以外,其他都只读到中学毕业,然后开始在周边打工。他唯一的儿子是老幺,老幺前面的三个姐姐后来一个留在西丽、一个嫁到清远、一个远嫁香港。邱新贵说,深圳生存的压力很多,自己家底薄,实在是对不住孩子。
儿子老幺上过中专,今年30岁了,不过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,这两年一直在外面搞装修,有活时就做一点,没有就在家待着。
老幺后来和深圳一本地女子结婚,有了孩子,但大部分用度还是来自邱新贵每年在山上的荔枝。
有一次,老幺在填写一张申请表,邱新贵指着“民族”一栏对老幺说,你还是不要填“汉族”了,改一个民族填吧?
老幺当时不明就里,问,那填什么“民族”好?
邱新贵戏称,填“啃老族”吧。老幺一下闹了一个大红脸。
戏说归戏说,但邱新贵的说法背后还是道出了“支农者”后代教育所面临的一些尴尬:这些年,邱新贵一直无法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,户口一直在紫金老家,孩子在深圳的教育出了多年的高价,当年小学每学期要多出600元借读费、初中要多出1000元,每年还要交劳务输入费、流动计生费、暂住费等等。
对此,邱新贵说,“你要问我这些年后不后悔,我还真回答不上来,”与同在紫金当年没有走出来的农民相比,邱新贵说生活还是要宽裕不少,在深圳的机会还是更多一些,总体上还是比没有出来的人强。
“最大的变化不在我们,还是在第二代身上,孩子们总体已经比我们这一代强出许多,一道前来的杨南风家就出了三个大学生,老魏家的孩子还在德国留学,这都是给我们种养场长脸。”邱新贵得意地告诉记者。
对此,深圳市人力资源与劳动保障局专家孟凡友博士分析指出,深圳早期的“支农者”无疑对深圳是作出过巨大贡献,但个人的发展也要与城市发展同步,要跟紧城市发展的脉搏。在30多年间,深圳已发展成国际大都市,其间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,也提供了无数人生发展机会,但邱新贵他们游走于这个城市之外,固有地坚持了自己的某些东西,没有在城市里完成转型。“这是遗憾的,却也是无奈的”。